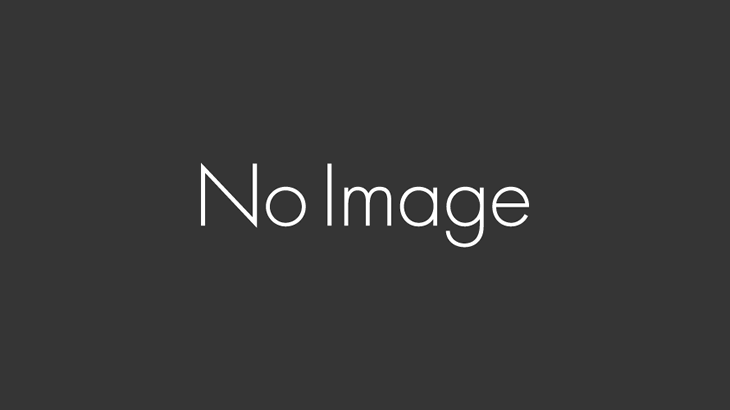地震的那一天,东京天气出奇的晴朗。
春潮蠢蠢欲动的三月天,微凉的气温中盈满亮眼的阳光,而天空就是东京一贯的那种接近透明而无限的蓝。
文=张维中
那天早上是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。学校在原宿的明治神宫附近,因此租借了神宫的礼堂作为举办场所。
全世界的典礼,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一样的。流程冗长而无趣,台上致词的人来来去去,台下的学生睡成一团。终于在结束的刹那,大家突然间清醒过来,苦苦熬到了拍照时间,每个人拿出相机开始东拉西拐的找人合影。
那时候所有人应该都以为,毕业典礼虽然乏味但应该就是那一天的最高潮了。但万万没有料到,更激烈的剧情原来还在后头。一场惊天骇地的地震,正虎视眈眈的等着我们。
散会以后,跟班上几个从台湾和韩国来的留学生,去学校附近原宿车站前的一间印度咖哩餐厅吃午饭。差不多连副餐饮料都已经喝完,聊天的话题也接近尾声,正觉得该结账离开时,我突然感觉到轻微的摇晃。
我是店里第一个感觉到地震的人。对身边的朋友说有地震时,大家因为还在聊天的兴头上,没有人听到。确实最初的几秒钟,只不过像是过去的小地震那样,以为没有什么大碍。但是很快的,震幅变得愈来愈强。也不晓得为什么,我直觉站了起来,立刻拿起背包,并且告诉同桌的友人,离开这里比较好。其实平常的地震,我不会这么做。但为什么却在这一次刚摇起来时,我觉得应该跑出餐厅呢?大概是先前才发生过纽西兰强震,而311地震之前在日本东北外海也震过一次,所以直觉以为可能会是场不小的地震。
就當我踏出腳步的剎那,整栋房子突然就像是被一只手用力握住,狠狠地甩了一下。这一甩,让整间餐厅里的人都意识到这不是场普通的地震。
我们用餐的那栋楼感觉很老旧。五层楼左右的楼房,从外观看来就不太像是够耐震的建筑。餐厅内的空间十分狭小又堆满瓶瓶罐罐,当房子愈摇愈夸张之际,我觉得要是再稍微用力摇几下,这楼肯定会垮。
当我们决定迅速离开之际,餐厅里的碗盘瓶罐已经哗啦啦的摔落下来。其实餐厅只不过在二楼而已,从回旋梯跑到一楼的距离也只有短短几秒钟,可是那过程却感觉非常漫长。在激烈的晃度中,移动起来彷佛泥菩萨过江。
终于,大伙都聚在一楼了,但震度并不削减,反而晃得愈来愈离谱。耳边开始出现路人的惊慌叫声,东西碰碎的声音。建筑因为摩擦与摇晃,发出了奇怪的声响。回头看见逃出的那栋餐厅楼房,在剧烈的摇晃下,开始掉落斑驳的灰。
要是这栋楼真垮了,就算我们跑出了餐厅,待在楼下也会活活被压死吧?
楼房的对面就是原宿车站铁轨外的人行道。那一侧没有楼房,应该比餐厅这一侧安全。我们于是决定冲向马路对面。
跑过马路的那一刻,地震的摇晃进入最巅峰。重心不稳的我拉起朋友的手,吃力的跨越过其实一点也不算宽的马路,往对面前进。
马路不可思议地像是波浪一样起伏,楼房跟电线杆无规则的急遽晃动。
所谓的关东大地震就是今天吗?就在我旅居于东京的此时此刻,发生了吗?
那样的摇晃令人开始感到无望。
头顶上的青空依然灿亮。朝气十足的阳光把世界照得充满希望似的,然而,却是袖手旁观着悲剧开始蔓延。原来灾难从来不是黑暗的;灾难可以是如此明亮,如此理所当然,坦荡荡的发生着。
抓着人行道上的栅栏,我却依然无法站稳。好不容易终于停下来,之后又历经了好几次强烈的摇晃。自此大大小小的余震始终没有停过。
不敢再回到楼房里,我们就近到空旷的明治神宫避难,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余悸犹存的人。直到傍晚实在愈来愈冷,无法继续待在那里时才离开。
可是电话不通、电车停摆、商店也关门,除了走路回家以外,没有其他方法。偏偏那天是毕业典礼,大家都穿着单薄的西装跟难走的皮鞋。女生更惨,有些人穿高跟鞋,有些人甚至还特地顶了一头造型过的头发,穿着繁缛的和服。这要她们怎么花几个小时的时间走回家呢?
几十万东京人就像是行军一样,任劳任怨花上好几个钟头走回家。在职场工作的朋友,干脆就留在公司。打烊的百货公司也开放让回不了家的人,得以进到室内避寒过夜。
在几乎交通瘫痪的东京市区里,我和朋友们结伴着,晃荡到夜里十点多才各自解散。
那天晚上的新宿还是个灯火通明的不夜城。很多上班族不想走路回家也放弃了排队搭车,干脆决定去唱KTV。因此连KTV也大排长龙。
当然,那时候还不知道核电厂发生问题,导致电力吃紧的窘态。大家虽然明白发生了严重的地震,但不清楚严重到什么地步。我跟许多流浪在外面的人一样,手机已经没电了(便利商店的电池充电器早被抢购一空),只能透过大楼的电视墙得知片段的消息。
到处都是无头苍蝇的人潮,四处都在排队。
前往我家的电车,终于在十一点半恢复行驶。不过,实在因为太多人,我又花了一个小时排队,才在夜里十二点半进站搭车。
直到回到家里再看新闻时,已经就是和大家一样透过媒体所见到的惨状了。
凌晨一点半,我风尘仆仆的回到家。打开家门的刹那,被眼前杂乱的景象给吓了一大跳。厨房的锅碗瓢盆、洗脸台上的瓶瓶罐罐摔落一地。电磁炉悬在流理台上摇摇欲坠,冰箱冷藏库的门开了一半,放在冰箱上的微波炉竟然整个跌到地上,外壳都变形了,电线却仍紧紧拉着插头,简直像是抓着大海里的浮木。
这景象比遭小偷闯空门还凄惨。我甚至花了好一番劲,才得以从玄关找到空隙踏进家门。
电视机里一个比一个还凄惨的画面交错着。在这个传播媒体发达的时代,全世界的人都一起目睹灾难的发生过程,却爱莫能助。
余震仍不停发生。我一边收拾,一边得随时警觉余震。心想要是愈摇愈大,就赶紧放下手边的收拾工作,做好逃生的准备。然而,事实是你永远不晓得这一次的摇晃会到怎样的程度。这一刻还安好的房子,下一秒,只要地壳再多释放一点气力,也许就会毁灭。听天由命向来就是地震的同义词。
整夜没有睡的我,直到清晨七点才终于体力不支倒在床上。
回到台北,又重返东京。「晕震」(地震酔い)的日子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月。
这一个多月以来,我和我的东京朋友们都处在一种「晕震」的状态里。晕震是日本媒体从晕船(船酔い)这个单字所改造的新用法,说的其实就是在余震不断的影响下,即使没震,却也老是会感觉好像在地震。
震度九级的东日本大震灾之后,整座日本列岛好像突然被开启了一个按钮似的,再也无法安定下来。光是震后一个月内的五级余震,就高达460次以上。在这种晕船似的晕震症状下,有好几次我在家里看书看到一半,都误以为又震了。结果,只是周围太安静而自己太专心,心脏跳动的错觉。
前两天走过陆桥,迎面而来的老太太突然驻足,直呼地震。周围的人一时之间被吓得全停住脚步。三秒钟过去以后,大家发现原来只是车子飞奔而过的关系。我和朋友安慰老太太,不是地震哟,可是,她却怎么也不相信。
许多住在东日本的人,这段时间都陷在类似的晕震里。有些人甚至严重到失眠,必须去就医。
因为余震太多,我的身体彷佛逐渐变成一座震度直觉判定器。每次震完以后,大概都可以判定,现在这样摇,应该是几级。然后打开网页一看,果然没错。
日本有一套地震紧急速报系统,会在震央发生地震后,立刻发送预报到接下来会感觉到强烈摇晃的地方。紧急速报透过电视也透过手机发送。八九不离十,确实都会在收到预知通报后的五秒左右,就开始感觉到地震。
虽然仅有短短的几秒钟,可是却有很大的帮助。至少你不会是完全无预警的。在讯息中你会知道身处的地方,可能将摇到几级。于是,你有心理准备,可以决定要有什么样的防范措施。快躲到家里安全的角落;赶紧跑到门边;或者干脆抓起救难包来。
我的手机地震紧急速报设定在三级。因为一级、二级的余震太多了,全都通知的话,迟早会被过多的预报搞到精神衰弱。三级地震其实并不算什么,但以「在室内需要心理准备」的震度来衡量,设定三级以上是刚刚好的。
紧急速报的地点是事先设定好的,所以当我回到台湾休假时,还是会收得到讯息。大地震的几天后我回到台北,还常常收到速报。当速报声音一响起,敏感的我就会立刻检查会有几级的地震来,完全忘了我人在台湾,并不会被震到。后来终于决定把它给暂时关掉,免得我也要去就医。
余震尚未结束,地震紧急速报经常响起,至于核电厂辐射外泄的问题迄今无法解决,各种余震的警告和网路上的流言讹语也未止息。
然而,时间仍然继续在走。对日本人来说,自从日本二次大战以后最漫长的一个月,终于也还是在四月初樱花盛开之际过去了。
那天上午,我准备晒衣服时,突然发现阳台上堆落着好几片樱花花瓣。
我有点惊喜也有些惊讶。在我家楼下并没有樱花树,它们会是从哪里飘过来的呢?
每一年期待樱花绽放的兴奋之情,有增无减。花开花谢,短暂的一个多星期,始终担心着只要稍稍不留心就会错过。
这一年,原本也有很多人跟我一样,再次期待着樱花盛开吧。可是,他们终究是没等到花季就被迫离开了。
我望向远方,还在找寻樱花来访阳台的方向。
灿烂的阳光,突然让我回想起地震的那一天。晴朗的午后,就在我越过马路的那几秒,有一刹那我是真的绝望的以为,大概一切都要完蛋了。抓着人行道上的栏杆,在猛烈的摇晃中,我除了向老天爷祈祷,又向在天国的我爸祈求以外,似乎已别无他途。
房间传来了广播的声音。
电台主持人说,福岛岩城市的小名滨地区今天宣告了「开花宣言」,开出了今年东北第一株的樱花。在被海啸席卷过的街道上,散乱的垃圾跟损毁的家具中,福岛地方气象台发现了这株樱花。
「海啸把雨量计都浸坏了,没想到被泡过水的樱花,还是那么坚强的开了。」气象台观察员说。
听着广播的我,捡起阳台上的一枚樱花花瓣,放在掌心,还没来得及仔细端详,一阵风吹来又把花瓣给吹走了。
逆光中,好似真的知道自己要去的方向。
・本文收录于张维中散文集《梦中见》联合文学发行